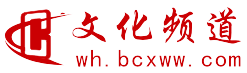|
学者们大多认为元散曲嘲讽、否定屈原,是元代楚辞学的一大特色。但在元诗中,元人对屈原既有肯定与同情,也有不赞同。 元诗肯定屈原主要是肯定其忠贞爱国的志行与高洁的人格。元诗对屈原忠贞爱国的肯定随处可见,如王旭《读〈离骚〉》“奸骨百年尘共朽,忠名千古日月光”,秦衡《题燕穆之楚江秋晓图》“愧我无才重吊屈,忠魂千古有谁招”,王沂《题屈原渔父图》则点出了屈原的“眷眷乡国心”,刻画了其至死不忘故国的忠贞形象。在肯定屈原的高洁时,元人则多以香草,特别是以兰入诗,对其进行称赞。如丁鹤年《画兰》:“湘皋风日美,芳草不胜春。欲采纫为佩,惭非楚荩臣。”此外,揭傒斯《兰》、郑元佑《题子昂兰》、张渥《题明雪窗兰》、马臻《移兰》等都表达了这一主题。元诗也对屈原的遭遇表示同情,如袁桷《挽王尚书四首》(其二):“楚泽痛灵均”,同情之心跃然纸上。这类作品还有卢亘《和阎子济韵二首》(之一)、柳贯《题离骚九歌图》、王冕《明上人画兰图》等。元诗对屈原的不赞同主要是反对其“独醒”、自沉汨罗。反对其“独醒”的元诗并不少见,如“一尊正候陶征士,莫学三闾爱独醒”(《次韵简苏昌龄学士仲铭禅师》)。又如谢应芳《和顾仲瑛金粟冢燕集》:“忍饥自作首阳鬼,独醒谁念湘江累”,许恕《丁酉午日前陈北庄》:“高咏楚辞茅屋底,汨罗谁吊独醒魂”。反对其自沉汨罗的士人,自古有之,仅汉代就有贾谊、司马迁、扬雄、班固等人,但元代诗人表现得尤其直接,喊出了“君莫学屈原,空葬江鱼腹”(于立《题醉卧图》)的话语。 元代诗人对屈原志行及人格的肯定,对其遭遇的同情等,大多历代有之,并无新意。而对屈原“独醒”、自沉汨罗的反对,虽不是首发,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心态。在元代,儒生的地位一落千丈,不仅没有稳定的入仕之路,还被种种不平的措施压制。元代科举时废时行,曾被废弃长达七十余年;恢复之后,又分榜取士,即使中举,也仍然没有出头之日。于是,士人们便认为“归隐山林”或“饮酒自醉”才是生存之道。在这样的背景下,元代文人在诗中否定屈原“独醒”、自沉汨罗也就不足为奇了。 元人对屈原的志行虽有不赞同,但对屈原的作品却十分喜爱推崇。元代理学家吴澄就曾说,孔孟而下,人们乐传以屈原为首的数十君子之文。在元诗中,也可见元人对屈原作品的喜爱,元人读《离骚》的情况,随处可见,如“一灯深夜读《离骚》”(周霆震《戏笔》),“晋帖临成思入石,离骚读罢拟栽兰”(刘清叟《寄朱约山》),“柴门尽日无人到,读罢《离骚》更煮茶”(李源道《暮春即事》)。 元代诗人不仅喜爱读《离骚》,在创作上也有意学骚。元初诗风承宋末,或承继四灵、江湖诗派,流于浮浅;或继承江西诗派,调字酌句,争奇斗怪。元人认识到这种流弊之后,主张“宗唐复古”,即古体宗汉魏晋,近体宗唐,以期扭转风气,这几乎是学界公认。但除此之外,也有部分元人认为只有自然而然地表达性情,才能进一步破除元诗模拟、浮浅之风,所以主张由汉魏上溯到风骚,继承风骚中的“性情之真”与“性情之正”。所谓“性情之真”即“性情流出,自然而然”(吴澄《王实翁诗序》),“性情之正”则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屈原的作品不仅得“性情之真”,也得“性情之正”。如朱熹所言,屈原的作品虽然辞旨“怨怼激发”,然“皆生于缱绻恻怛,不能自已之至意”,是一种自然流出,不能自已的真挚情感。屈原的作品也并不是“怨君”,而是寄寓了其“忠君爱国眷恋不忘之意”,在客观上可以起到“正人心”的作用,合乎儒家“吟咏性情之正”的诗教理想。元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如吴澄虽然认为诗“古祖汉,近宗唐”(《胡助诗序》),但其也认为《诗》《骚》“性情流出,自然而然”,所以他也说“言诗,颂、雅、风、骚尚矣”(《诗府骊珠序》)。如虞集认为屈原的《远游》得“性情之正”,其言:“《离骚》出于幽愤之极,而《远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与泰初以为邻。”(《胡师远诗集序》)此外,赵孟頫也曾在《南山樵吟序》中引黄庭坚之言,强调作诗要“本之以《国风》《雅》《颂》,深之以《离骚》《九歌》”。 这些诗人不仅在诗学理论上主张人们学骚,也进行了创作,皆有骚体诗传世。如吴澄有《泗滨四章》《楚歌五阙劝潭士归乡》《题芦雁飞鸣宿食图》《楚语赠欧阳尚古》等,虞集则有《钓雪操》《思鲁琴操》《东山操》《题柯博士九疑秋色图》等,赵孟頫则有《杨坚州治水歌》一篇。即使不着重学骚的诗人,也在客观上受到楚骚的影响,如胡应麟《诗薮》说揭傒斯“师李,旁参三谢”,但其也有《桂林歌赠胡秀才》《新安许氏兰秀轩》《所藏远山图》《题陈氏松巢图》等骚体诗。据学者统计,元代诗人创作了将近340首骚体诗,占元代骚体作品总数的一半以上。 元代骚体诗对屈原作品进行了模仿。首先在体式上,元代骚体诗主要采用《九歌》的体式,也有一些作品用《离骚》体和《橘颂》体,如陈义高的《望乡歌寄卢疏斋》交错使用《离骚》体和《九歌》体,句式较为灵活。除了体式上的运用,有的骚体诗直接在序言明是模拟屈原作品之作,如沈贞在《乐神曲并序》中自言:“乐神曲,拟楚词九歌而作也。”有的作品虽然没有说明,但直接引用了屈原作品中的字词、句子。如陆仁《题文海屋洛神图》一诗,直接引用了《九歌》中的“折芳馨兮遗所思”“目眇眇兮愁予”两句。黄玠的《浴兰之歌叹往事也》,以及于钦的《巢湖中庙迎神歌》《送神歌》等对《九歌》皆有不同程度的引用和化用。 但元诗学骚,最终只是停留在对体式、字句的模仿上,并没有深入其内在的精神气质。元代骚体诗往往也慨叹社会的不公,宣泄人生失意的痛苦,表达壮志难酬的郁结。如吴澄的《题芦雁飞鸣宿食图》,其诗曰:“败芦兮萧萧,肃肃兮嗷嗷。警夜兮泬寥,为一饱兮辱泥滓以劬劳。鸿冥冥兮九霄,侣大鹏兮逍遥。”芦雁为求一饱,忍辱劬劳,但却始终无法“上九霄、侣大鹏”。吴澄以芦雁喻人,揭示了有元一代文人空有才华却无法展示的悲哀。但当元代诗人遇到这种不公的时候,却没有像屈原那样对统治者表达怨愤,更没有直接批判社会的黑暗,也很少在浊世中坚持自己的理想,以“苏世独立,横而不流”的态度对抗世俗,反而想要逃避到山林中,纵情山水、及时行乐。所以元代出现了大量以隐逸内容为主的骚体诗,如袁桷《岳麓图辞》、王逢《小山招隐辞》、郑玉《招隐辞》、傅若金《松涧引》、胡炳文《送邹云樵歌》等。这些骚体诗大多吟咏山水,描写隐逸生活的美好,虽然偶尔也能看到作者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但都比较温和,并无批判当时社会黑暗不公,谴责君王忠奸不辨的锋芒。 胡应麟《诗薮》点评元诗云:“元之失,过于临模,临模之中,又失之太浅。”元诗学骚亦是如此。元诗学骚,本意是破除模拟、肤浅的流弊,但最终却只是沿袭了屈骚的表达方式而失去了其本质和精神。缺少了深厚的文化含蕴和深沉的悲剧意味的元代骚体诗自然深意不足,明人认为其微不足道也有一定道理。(陈静) [365赌网app官网_365bet论坛_beat365官方入口新闻网编辑|陈硕 复审|赵翠丽 终审|贾涤非] (责任编辑:审核发布) |